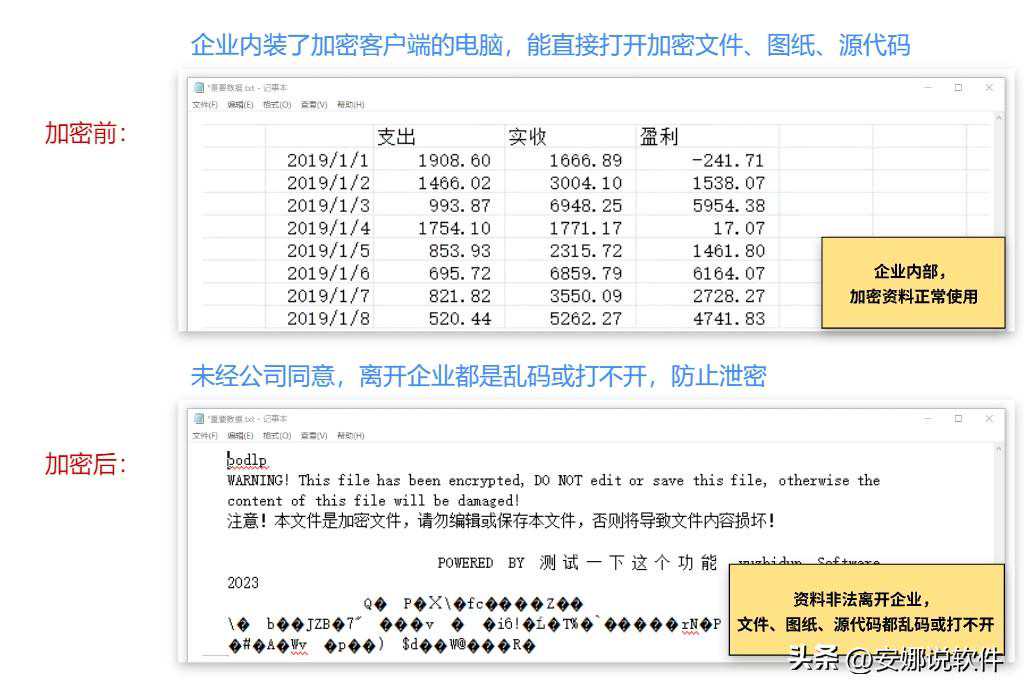摘抄|街巷沐足(二十五)
 admin 2025-03-18
112
admin 2025-03-18
112
摘抄
在街巷沐足,太便宜了,二十五元。
整条街的各个缝隙里,都塞着沐足的广告牌,价格从八十八至六十八,至四十八、三十八……直至二十五。想一想:一个活儿(八十分钟),又捏又捶,免费提供雪碧、可乐、茶(任选一样),真的不贵。
这间屋子里有三张沙发床,大吊灯,空调,电视,一个圆盘大表,门口挂着电话,看起来和酒店包厢里的摆设差不多,但细一看,质地粗糙,加上外围环境嘈杂,不得不用降价来揽客。
她进来时,我大惊:皮肤赢黑,五官平淡,头发稀疏,白衬衫裹在腰上,几乎要裂开,黑短裙下两条腿,壮如大象。“338号,起钟。”她拿起电话,气贯长虹地说。
她上岗才三个月,但我选择的二十五元的标准,只能提供这样的新手。
她往脚盆里铺了层塑料薄膜,给我的脚喷了酒精后,让我泡进去,伸出瘦骨嶙峋的大手,开始按摩头、颈。当她的手指弹奏起来时,她的长相变得模糊,而只剩下一双手,独一无二的.表现力极强的手。
仅仅四个月前,她还站在湖北荆州自家的稻田里。那一天,她从田里走回家,脱下沾着泥巴的胶鞋,抹了把脸上的汗,和丈夫说了声后,拿起个馒头,拽起外套,到了火车站,直奔厚街而来。
她已三十岁,已有两个上初中的女孩,又生了一个男孩,罚款八万。而她,居然在这之后……又生了一个女孩!当然,还得交罚款。
现在,那孩子的年龄是“一把抓”。看我不懂,她咧嘴大笑:“哈哈,是五岁。”她说她喜欢生孩子,说孩子贴心,比死鬼男人靠得住。
然而,四个孩子一年开销要一两万,单靠卖稻谷的收入,
显然无法维持。钱怎么用总是引发她和老公打架的导火索。
她老公脾气暴躁,从刚结婚开始就打她;过了几年后,她也开始打他。
总是打得天昏地暗。她有一身力气,未必次次都会输。打完后,两个人将脸上的血抹一抹,再商量钱怎么花。最后的结果是:老公在家种田,她出门打工。
交多了三百元,上了培训班,她学得格外认真。“吓,开除了好
多人呢!”她瞪圆眼睛。师父是个帅哥,教她们认人体穴位。
可师父的手很难看:食指关节粗大。那是长期按摩的结果。学员们叫嚷着说累,可她并不觉得比晒着大太阳插秧更难——还要站在水里!学完理论,先给师父按一遍,他说行,才能挂牌上岗。
她待的这家沐足城实在太小,不发工资,全靠提成(二十五元可提成十元),一个月的收入接近两千元,包吃包住,一间屋睡六个人,一天两顿快餐。中午12点开工到深夜1点,少时六个客人,多时十几个。
洗脚时,她专注地盯着脚看,像医生面对病人。每个客人都被她浓缩成一双脚。只要她开始干起来,便一心一意,让每个动作都落在实处,不偷懒,不耍花招。
“我们把内力传出去,客人舒服了,我们就疲劳了。”
虽然她只干了三个月,可她已经有了几个回头客:客人认的是她的手法,无论她再老、再丑。当然,她也不是没有受到过冷落。
有人一看她的长相,即刻挥手:“换人!”她虽然尴尬,但转念一想,“我靠劳动吃饭!怕什么?”又变得坦然。
在338号的语汇中,“劳动”这个词,还保有过去年代的荣光。她那么想挣钱,却拒绝了一桩美事:有个中年男子来洗脚.一连来了好几次,左右盘问,晓得她这个人实在,舍得出力,遂提出让她到他家照顾他父亲的起居,工资比这里高一倍,春节可放假,年底有红包。他掏出张照片:一个矍铄老人,干干净净,坐在藤椅上晒太阳。然而,她愣怔了半晌,还是摇摇头。
她不愿意。
她在这里靠手艺吃饭,虽然提成不多,但过得坦然;到了他家,他就变成她唯一的主顾,无论他提出怎样的要求,似乎她都不能拒绝。如果他家确实需要保姆,可以直接去中介公司找,何苦这样?那种模糊地带的幽暗,令她顿生警觉。
在她看来,从稻田里拔出泥脚,挤上火车,来到城里当技师,并非跨界,不过都是凭力气吃饭。但她却不能接受那貌似轻松却充满暧昧的工作。
不,那才是真正的跨界。在她的经验世界里,无论任何人或任何事,都各有其界限,若强行越界,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
很简单,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?
她现在最大的理想是:坐在沙发上,让别人来洗脚。
- 同类文章
- 友情链接
-